男女主角分别是刘清宁王静的其他类型小说《两万里路云和月全文》,由网络作家“茹若”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李阿四热络地给三人添茶:“小陈镇长,这是镇里新来的领导?”吴楚楚道:“阿四叔,你不认识我?我是美莲的女儿!”李阿四一拍大腿,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哦哟,永梅姨的外孙女!是吧?”“是。”“上次在向远店里见过嘞!”“没错。去年还是前年的事了,你记性真好。这是我表妹,宁宁。”“哦,宁宁阿囡!小时候见过,我还抱过你呢!”知道是熟人,几个老人迅速热络起来。躺在竹摇椅里悠闲自在地摇着扇子的老嬢嬢,年纪不大,中等身材,白面皮,短发烫着小卷,染着和眉毛一样的红棕色,耳朵上挂着两个金晃晃的耳坠子,财气十足。两姐妹不认识,李阿四介绍,是位归国华侨。年轻的时候出去闯,辗转南洋,欧洲,最后在巴西住了三十多年,普通话都说不好,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巴西语。听说她有...
《两万里路云和月全文》精彩片段
李阿四热络地给三人添茶:“小陈镇长,这是镇里新来的领导?”
吴楚楚道:“阿四叔,你不认识我?我是美莲的女儿!”
李阿四一拍大腿,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哦哟,永梅姨的外孙女!是吧?”
“是。”
“上次在向远店里见过嘞!”
“没错。去年还是前年的事了,你记性真好。这是我表妹,宁宁。”
“哦,宁宁阿囡!小时候见过,我还抱过你呢!”
知道是熟人,几个老人迅速热络起来。
躺在竹摇椅里悠闲自在地摇着扇子的老嬢嬢,年纪不大,中等身材,白面皮,短发烫着小卷,染着和眉毛一样的红棕色,耳朵上挂着两个金晃晃的耳坠子,财气十足。
两姐妹不认识,李阿四介绍,是位归国华侨。
年轻的时候出去闯,辗转南洋,欧洲,最后在巴西住了三十多年,普通话都说不好,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巴西语。听说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巴西,生意做得很大。
“我今年才六十五,年纪小辈分大,你外婆都要叫我姑呢。你要叫我阿太了!”老嬢嬢说道。
“你们该叫她姑婆太!”李阿四指点着。
两姐妹顺从地叫了一声“姑婆太”。
角落里的睦竹椅上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嬢嬢,穿着一件老式的蓝布衣,从三人进来开始就没说话,只是微笑。
李阿四介绍,这是万斋婆。
刘清宁想起来了,万斋婆是万斋公的老婆,万斋公是一个高大的老头子,教了一辈子书,退了休没事做,日日在路寮跟人闲谈、下棋。
云上村的孩子们玩闹,看见万斋公坐在路寮里便远远绕开,因为一旦被他抓住,他就要摇头晃脑起来:“娒儿,几年级了?我来考考你......”
后来万斋公走了,万斋婆就一个人过日子。听说她生过几个孩子,都死了,好不容易养大了一个,90年代跟人出国,再没有消息。
听外面回来的人说是死在半道上了,但没人敢告诉她,只说联系不上。
下山的时候陈今越告诉姐妹俩,自从小儿子也没了,老嬢嬢的精神就有些不正常,有时候一天到晚一句话不说,只是笑。
两人童年的回忆,随着与几位老人“相认”,全从记忆深处不住地冒出来了。
“阿太,你家人都在巴西,你怎么不留在巴西?”刘清宁问。
阿太躺在摇椅上扇着蒲扇,半睡半醒的样子十分惬意:“巴西哪有家里好?我住不惯那个地方,也吃不惯那里的东西。年轻的时候要赚钱没办法,后来又要帮儿子带孙子,没办法。”
“你不知道,她有二十多个孙子外孙嘞!”李阿四插嘴。
二十多个,刘清宁听着都要晕过去了。
“可不是吗,带了孙子又带重孙子!现在老头子不在了,我一个老嬢嬢,是该休息的时候了,他们生个不停,我可带不动了,我就逃回来了!”
哄堂大笑。
阿太在摇椅上挪了挪身子,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回来好啊,家里吃好喝好,病都少了,这才叫好日子呐!”
“这话没说错!”李阿四十分赞同,扯着大嗓门发表意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和种田一样的,我们南方就种水稻,他们北方就种小麦,我们南方硬要种小麦,那肯定水土不服!我们中国人就该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吃中国的土地种出的大米蔬菜,身体就会好,病就少了!”
“那你不想孩子吗?”
“想啊。哎,但是没办法。我说让他们有空了回来看看我,都说好好好,结果呢,你看看,我回来都五六年了,一次都没回来过。”阿太叹气,“哎,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赚钱去国外,把孩子们丢在家里,也是几年回不来,现在老了,风水轮流转喽!”
她说完便轻轻地笑起来,摇着蒲扇和摇椅,仿佛十分惬意的样子,但那语气中一丝丝的遗憾,随风飘散之际,却被刘清宁敏锐地抓住了。
李阿四弓着背,拎着茶壶从屋里出来,给几人都添了茶,嘴里念叨:“子女缘天注定,跟我们两个比,你算好的了。”
“好什么,殊途同归,现在都是孤单单一个。”
“有我们两个陪你呢,不算孤单。”
众人都欢乐地笑了,安静地坐在一旁的万斋婆也轻轻地笑出声来。刘清宁端起茶碗,这次没有一饮而尽,而是小口小口地品着这苦中带甘的滋味。
喝着喝着,突然觉得不对劲,背后发凉。
“阿四叔,这村里现在就住了你们三个?”
“没错。”李阿四比划着,“我们三个现在是相依为命。”
两姐妹对视一眼。
那么刚才看到的那个,还是鬼?
山谷寂静,山风拂过山岗,穿过路寮,从后颈的衣领钻进去,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吴楚楚咽了咽口水,无声唱起歌来。
从前看完恐怖片晚上不敢睡她就唱这个,管用。
陈今越看了看两姐妹的样子,料定她们两个刚刚撞见过老吴了,敲了敲桌子,笑:“阿四叔,你别胡乱说话,吓得她们两个脸都青了。那后头的大宅还住着一个,这村里现在就这四口人。”
“噢!”两姐妹擦了擦鬓角的冷汗。
李阿四硬着脖子:“你当他村里人,他自己不认呢!”说完又低声嘟囔:“这冷屁股要贴你自己贴,我不贴。”
阿太摇着扇子:“你别同他说,他们两个有私怨。”
“谁跟他有私怨?是他对不住我,骗光了我的养老钱。嘿,老天爷也看不下去,让他儿子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行了。”眼看对方越说越不像话,陈今越不得不端出架子,正色道:“李阿四同志,你现在是村里的网格员,也好歹是半个政府的人了。面对群众,怎么能夹带私人情绪?”
“政府的人”这四个字,显然让李阿四很受用。刘清宁注意到,陈今越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尽管脸上还很是不服气,嘟嘟囔囔地小声反驳,但李阿四的胸脯不由地挺直了,昂头挺胸,十分骄傲。
她忍不住噗嗤笑了。
临走的时候,阿太拉住陈今越问:“小陈镇长,前头我和你提的老人食堂的事,镇里有消息吗?”
陈今越耐着性子解释:“阿婆,我同你讲过了,你们就这么几个人,搞老年食堂不现实。就算你肯出大头,这点钱也办不下来。不如你听我的,搬到山下去住。”
阿太摇头:“我不去。我要住在自己家里。”
陈今越无奈:“那你自己小心,阿四叔,万斋婆,你们都是。隔夜的饭菜要少吃!”
“知道,知道了。”
“你们就敷衍我!”
回去的时候,三人沿着山路拾级而下。
正午的阳光炙热,山脚下是一片粉墙红瓦的新楼,鳞次栉比,反射着刺眼的日光。青山如黛,一切都是崭新的模样,这种新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让人心情愉悦。
与这山脚下崭新的、蓬勃的新村庄相比,山上的云上村显得更加衰败。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承载着她童年快乐记忆的小村子,或许就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临近清明,淅淅沥沥地下了半个月的春雨,真到了清明时节,天却放晴了。
清晨,薄雾弥漫在瓯江上。
张阿婆凌晨就起来忙乎,天刚擦亮就把摊子摆了出来,占据了华侨酒店门口最佳的位置。
虽是清晨,酒店大堂却并不安静,间或有远道而归的出租车在大堂停下,下来两三个风尘仆仆的乘客,卸下三四个塞得鼓鼓囊、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的红白蓝编织袋。
张阿婆的儿子儿媳妇都在华侨酒店上班,说这前后半个多月,城里的酒店全满了,住的都是从国外赶回来扫墓祭祖的华侨人,小两口天天忙得脚不着地,加班到半夜才回家。
回来好,回来好啊。
这城里乡下的,不都热闹起来了吗,她的萝卜丝饼摊子不就忙活起来了吗。
这青田城里乡下,一年到头最热闹的,除了过年就是清明,也是她的萝卜丝饼摊子生意最好的时候。
张阿婆年纪虽大,但耳朵还灵,尤其是听到手机时不时地响起:“微信到账XX元支付宝到账XX元”的时候,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又一辆出租车在酒店大堂前停下,下来两个女人,像是两母女。一对等在大堂门口的中年夫妻急忙迎了上去,帮着从出租车上卸下整整五大袋行李,手忙脚乱地往明亮的大堂里拖去。
年轻的女人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没有急着跟进去,反而裹了裹风衣,打量起周围的环境。目光在街道上逡巡了一圈,最终落在她的萝卜丝饼摊子上。
迟疑片刻,女人还是裹着风衣过来了。
四月的早晨还凉,刘清宁裹紧了风衣,迟疑地开口:“一个萝卜丝饼。”
张阿婆麻利地掂起大圆勺子:“蛋要吗?”
“要。”
乳白色的面糊倒进油锅里炸热的大铁勺里一滚,再放进油锅略炸几秒定型,掂起勺子,铺上萝卜丝、瘦肉碎,再敲一个鸡蛋,压实后盖上面糊,送进油锅里炸。
“哪回来的?”张阿婆随口拉家常。
“马德里。”
张阿婆点头:“哦,马德里啊。我小儿子以前也在马德里,这几年去罗马了。”
说话的功夫,一个炸得焦脆香酥的萝卜丝饼便出锅了,放在油锅上方的铁丝架子里凉却滤油后装进油纸袋:“八块。”
小时候才五毛钱一个呢。
刚炸出来的饼,油香,酥脆,一口咬下去,油香裹着萝卜丝的清甜在嘴里嚼碎混合,还未冷却便顺着食道落到胃里,这份熨帖是那些干巴的欧式面包给不了她这颗中国胃的。
她裹了裹身上皱巴巴的风衣,捧着烫手的萝卜丝饼,目光所及之处,浓雾渐渐散去。在飞机上睡了十几个小时,从上海到青田的这一路,刘清宁却清醒得很。眼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从繁华的上海都市到寂静的脉脉青山,天上的星光淡下去,天边透出微弱的曦光,横亘瓯江的太鹤大桥在清晨的江雾里若隐若现。
此时,太鹤大桥在缭绕的雾气中逐渐清晰。
陌生又熟悉。她已经有些想不起来这桥从前的样子,是一贯如此还是重新修整过了?
离开青田的时候她十二岁,如今归来却已经二十五了。
十三年前,她坐上飞往马德里的飞机时,未曾想过自己离开这么多年。
前几年是因为年纪小,没有父母的陪同无法单独回国,后来习惯了马德里的衣食住行,便渐渐地也没了念头。
父母店里忙走不开,她学业忙走不开。总想着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回国,等一等,再等一等,明年吧......但没料到的是,有的人却等不了。
外公走的时候,家里的超市还没开起来,条件还不好,父母都在华人老板的商店里打工,请不起假也买不起来回的机票。没能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母亲王静在电话里对着大姨痛哭了一场。
后来攒了点钱,父母开了个小超市,条件便好起来了。
外公走后,外婆的身体便渐渐大不如前,趁着这次清明,王静下定决心回国一趟,除了给扫墓之外,也是要再在母亲面前尽尽孝。
天边破晓,天也渐渐亮起来。
刘清宁躺在酒店柔软的床上,瞪着眼睛看天花板,身体倦困,可意识却随着落地窗外逐渐亮起的日光而清醒起来,耳朵里飘进大姨王美莲和妈妈王静的低声私语。
“吵得厉害,已经回娘家好几天了。我上了好几回门,面都不见。”
“怎么这样?那妈现在呢?”
“二哥看着呗,没办法。保姆也不好请,老嬢嬢脾气倔,请了几个都做不久。”
“那怎么行,二哥一个男人,怎么会照顾人?”
“那没办法。我让她到我这住,第二天就把东西收拾起来说要走,住不牢!”
“城里面她哪住得牢!”
“那没办法呀!”
这说的是刘清宁的二舅和二舅妈。据刘清宁所知,二舅家闹“家变”已经闹了小半年了,王美莲每每跟王静通视频电话,都要讲到这个事情,唉声叹气一番之后,又要把二舅妈一些陈年烂谷子的事情捯出来说一遍,导致那些故事刘清宁已经倒背如流,对二舅妈也没什么好印象。
二舅王向远年逾六十,原本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谁知道这两年国家放开计划生育,两个儿子响应国家号召,前后脚怀了二胎。
大儿子一家住在市里,二儿子一家住在县城,二舅妈李丽琴照顾两个儿媳的孕期,原本就是顺得哥情失嫂意,焦头烂额,偏偏不久前刘清宁的外婆又病了一场进了医院,病床边上离不开人,二舅在村子里开着一间小超市,吃穿全靠这点收入,照顾病人的活自然落在李丽琴的头上,结果两个儿媳妇又闹了矛盾,含沙射影地发了几个朋友圈,李丽琴一气之下撂挑子跑回了娘家。
手机铃声响起,聊天的声音戛然而止。王美莲接起电话,才喂了一声,随即“啊呀“一声惊叫起来。在这静谧的清晨,这惊叫声像一把利刀子,将刘清宁刚刚袭来的困意瞬间划破。还不等她听清楚,房间里便嘈杂喧哗起来,三个长辈的声音此起彼伏,混乱得如同一团乱麻。
王静匆匆把手机塞进随身携带的小包。
“妈,怎么了?”刘清宁压低声音问。
王静半秒都没停留:“你外婆喝药自杀了!”话音未落,三个人带着慌乱消失在客房门外。
刘清宁茫然了几秒,从床上跳了起来。
阿青婆生于民国初年,长于战争年代。具体的时间没有人记得,应该是1930年以后,她嫁到云上村,没几年,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个年代,农村的日子并不好过,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几年,阿青婆的丈夫,陈显华的爷爷陈定为了谋生,丢下家中的妻儿,跟着同村人一起去了欧洲,从此音讯全无。
那个年代青田人出国打工,并不走正道,死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数。
阿青婆等了又等,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村里人都默认他已经死了,还有人劝她趁年轻改嫁,但阿青婆始终没有答应,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养大。
那是个战争的年代,除了应对自然灾害,还要提防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日军的飞机炮弹。
1942年,日军攻陷青田,云上村虽然偏僻,但没能逃过日军的搜掠。
“我父亲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常常同我讲起以前的事。”
那时陈建明已有八九岁年纪,他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搜掠,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躲进屋后的地窖里,年幼的妹妹忍受不了地窖的湿闷,大哭起来,引起了鬼子的察觉,
母亲拼命捂住了妹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才逃过一劫,等鬼子走了之后才发现,因为捂得太紧,妹妹已经闷死在母亲的怀里。
当时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多年以后提起来还心有余悸,而母亲因为闷死了妹妹而愧疚,精神大受打击而病倒。
但即便病倒了,她还是得拖着病体下地干活,挣钱来奉养公婆,照顾两个儿子。
可以想见,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阿青婆过的是怎样艰辛的苦日子。
后来,红军打跑了鬼子,解放军渡过了长江,成立了新中国,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大约是五十年代,阿青婆收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消息,原来陈定并没有死。
“这事村里人都知道!”李阿四说,“那年我还是个小后生,听我娘说,村里回来个华侨人,是阿青婆的男人,有钱呢!啊哟,不得了,穿西装,打领带,皮箱里都是洋货,后头那座石桥,就是他捐的钱修的,桥头碑上还有字嘞!嘿!原来那就是你阿公!”
那时云上村的人才知道,当年虽然陈定的目的地是欧洲,可是他上错了船,糊里糊涂地跟同村人分开,孤身一人被带到了南美,最后在巴西上了岸。
在巴西,他做过一段时间提包挈卖的营生。
所谓提包挈卖,是海外青田人积累资本最原始朴素的方式。
扛着一个编织袋,装着鞋子、衣服等杂物百货,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那时候闯天下的青田人,没有人脉,没有门路,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活开始干起。
在提包挈卖的那段日子,陈定认识了一个当地华人的女儿,很快和对方坠入爱河,缔结婚姻。
在新岳父的资助下,两夫妻到了西班牙,开了餐馆,做大生意,赚了不少钱,成了大老板,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阿青婆是什么反应,已无人知,但不难想象。
陈定在云上村住了半个月便走了,这一走就再没回来过。
后来陈定写信来,问阿青婆是否愿意出国,阿青婆拒绝了。
她收下了陈定寄回来的钱,推倒了陈家原本的破牛棚,重新盖了房子,便是现在的陈家老屋。
建新房子的时候,阿青婆只给自己在一楼留了房间,东西两侧各起了二层小楼,留给两个儿子一人一栋。新房建成,又大儿子陈建明娶了老婆,生了一儿一女,阿青婆的脸上,日日都是喜气。
她还有儿子、孙子,村里给她分了地,有田种,有饭吃,日子蒸蒸日上,没了男人,不算什么。
好景不长。
五十年代末,全国上下遭遇了大饥荒,到了六十年代初,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为了谋出路,陈建明带着妻子和弟弟,搭路子出国投奔父亲,也在西班牙定居,只留下五岁的大儿子和三岁的女儿,也就是陈显华的大哥大姐给阿青婆抚养。
阿青婆不得不又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职责。
70年代末,两个成年的孙子孙女也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从此,老房子只剩下阿青太一个人居住。
“一直到新房子变成老房子,然后在这房子里孤零零地去世?阿青婆真是可怜。”刘清宁说道。
“其实,我父亲也想接她到西班牙一起生活。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奶奶来过马德里,还住了一年,所以,我对她有一点印象。”
在陈显华的印象中,奶奶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老人。
她一直穿着很旧的蓝布衣衫,是那种传统的中国样式,衣领袖口还绣着中国样式的花纹。
她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说西班牙语,而是讲口音很重的青田方言。
那时候,陈显华不会青田话,如听天书一般,根本无法与奶奶交流。
阿青婆被接到马德里的时候已经年迈。
那时候,陈显华的祖父已经去世,他的继奶奶是陈家的大家长,在马德里,她唯一认识的只有自己许多年未见、并不熟悉、忙于生意的两个儿子和由自己抚养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
听到这里,刘清宁忍不住想起了刚到马德里的自己。
当初登上前往西班牙的飞机,阿青婆肯定和她前往马德里之前一样,是对未来的生活抱着一种期待的,她盼望的是与从未谋面的父亲、分离多年的母亲的重聚,期待的是父母疼爱的怀抱,阿青太盼望的、期待的则是母子团聚,一家团圆,从此颐养天年。
但很显然,她们都没能如愿以偿。
父母疼爱的怀抱,是属于她的弟弟妹妹的。而一家团聚颐养天年,则是属于那个抢走阿青婆的丈夫的女子的。
长久的分离,文化的隔阂,是她们和家人之间迈不过去的鸿沟。她们都成了这个家庭的“旁观者”,就像西方电影里那种死去之后留在家里的亡魂。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愉快。
六月一过,酷暑将至。
云上村海拔高,气温低,最适合夏日避暑,趁着天气还未大热,祖孙俩搬进了老屋。
老屋是独栋结构,两层,直排样式,连带前门开阔的院子,占了近一亩地。
正屋坐北朝南,左右对称。沿着中轴线,左右各有两间。
重檐悬山顶,抬梁、穿斗混合式梁架,阑额、牛腿、雀替、门窗雕花样样齐全,屋里的家具多是民国时期样式,四方餐桌,虎脚大衣柜,五斗橱上雕花精细,连把手都是铜制的,把手底座是镂空吉祥如意祥云,样样十分精美,可见当年王老裁缝家底颇丰。
王永梅的房间原本在二楼,年纪大了腿脚不便,祖孙俩商量了一番,收拾了一楼东边原本的杂物房,将原先的雕花床,五斗柜都搬了进去,再略作布置当作卧室。
房间不大,但推窗便是景,老嬢嬢十分满意。
二楼原有六个房间,翻修的时候,刘清宁打通了中间的两个,做了个前后通风的客厅,窗子一开,凉风习习。
东边朝南的房间是王静的卧室。刘清宁婴幼时期跟着王静在这里住过几年,那时太小,没什么印象,但从前每逢寒暑假,两姐妹回外婆家,也住这里。
刘清宁选了这个房间自己住。
老屋的东侧,原本是猪栏和旱厕,翻修的时候让工人全部推翻填平,只留下了那棵老石榴树。
正是石榴花开的季节,郁郁葱葱的绿叶之间点缀着火红的花,十分好看。等秋日结了石榴,坐在树底下喝茶吹风赏月,想起来就十分惬意。
除了厨房和上下两个卫生间做了比较大的现代化装修,地面做了硬化之外,屋里其余的部分,一应家具,还是从前的样子。
一来是想最大程度保留外婆和自己的回忆,二来实在是经费不足。
镇里村里都在传她拿了镇里十几万,实际上拿是拿了,却并没有那么多。付了工程款,又购置了一些家电家具,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倒欠小舅五万块,还得想办法还。
刘清宁觉得,自己这口“黑锅”背得实在冤枉。
七月的傍晚,小院里晚风习习。
煤球炉上煮着端午茶。
“连吴楚楚都问我,说二舅妈的两个儿媳妇为这事又闹起来了,二舅家里鸡飞狗跳。我小舅妈也打了电话来,旁敲侧击。我实话实说,就拿了镇里十万块,全花完了。一笔一笔,都记着账呢。”
最初的时候她计划好了,满打满算,手里就十多万,先抓要紧的修,除了厕所和厨房,能将就的先将就,以后再慢慢添置。
真开始干了,才发现老屋的状态实在差,该修该补的,这钱不能省,那钱也得花,没过半月,花销就大大超出了预算。
后来陈今越帮忙,从镇里申请了十万块老屋修复基金,花下来也所剩无几,如今看着银行卡里那点儿可怜的余额,恐怕要不了多久,祖孙俩就得过上喝西北风的日子了。
“我奇怪的是,这事我谁也没说,是怎么传出去的?”
陈今越支着一只腿,半靠在竹椅上,嘴里还叼着一支不知道从哪里扯来的狗尾巴草,半眯着眼睛听刘清宁抱怨,不回答,只是笑,满脸写着“你猜”。
刘清宁想了想:“阿四叔?”
“嘿!”她真猜到了。
“真是他呀!”
“我可没告诉他多少钱,纯粹是他自己猜的。”陈今越给自己撇清关系。
刘清宁撇嘴:“你还真是知人善用。”
李阿四在村里有个外号叫“喇叭四”,话又多又密,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包管第二天就人尽皆知。
陈今越看出她有点不高兴,不由地坐直了身体,轻咳一下:“一点做工作的小聪明,不值一提。”
做了大半年的农村工作,陈今越总结出一点小心得来。政府的政策,你敲锣打鼓地宣传,他们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不进去半个字。你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他们反而绞尽脑汁要来打听,千方百计地帮你宣扬出去。
他将计就计,把给了刘清宁一笔修复老屋的补贴的事装作不经意地在李阿四面前说漏了嘴,又一再叮嘱他不要传出去,果然不出三天,整个云林镇都传遍了。
镇里又要搞云上村的项目了!发动村民修老屋,给补贴!王永梅家的老房子拿了几十万补贴呢!
“只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把金额传得这么离谱。”他真诚地道歉。
刘清宁倒也没真生气。
“算了,我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你救了外婆,帮我找施工队,又帮我申请翻修补贴,我该谢谢你。上次吃饭还是你付的钱,等过些天,我这都收拾妥当了,请你来家里吃一顿便饭。”
“别客气。你谢我,我倒还要谢你。要不是你给了我提示,我还解决不了纸板婆的问题。”
“谢我?”怎么还与她有关?
刘清宁惊讶。
虽然不认识纸板婆,但关于她的事镇里都在传,刘清宁自然知道。镇里人都说,小陈镇长的脑子活,好几年解决不了的事情,让他三两下就给解决了。
陈今越一脸得意:“想听?”
“听听也无妨。”
水烧开了,刘清宁起身,给陈今越满满地续上了一碗凉茶。
刘清宁没能追上王静一起去,等到表姐吴楚楚过来接她赶到医院的时候,外婆王永梅已经从急救室出来了。
医院的惨白色灯光永远让人心底茫然。
去医院的路上,刘清宁想起从前和外婆相处的点滴,大部分记忆都已经模糊,只记得外婆对她和表姐这两个外孙女分外疼爱,每年秋天,老屋后门的两颗板栗树成熟,收下来的板栗,总会仔细挑最好的,藏起来留给她们。老屋周边还有几棵柿子树,柿子不耐储存,就晒成柿饼,收起来等她们放了寒假来吃。
还有五月的枇杷,六月的杨梅,一别十三年,再没有吃到过外婆特意留给她的果子。
“外婆为什么要喝药?”她想不明白。
吴楚楚一脸凝重,没有直接回答:“还不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老嬢嬢一时想不开。唉,说来话长,不过都是长辈的事,我们别掺和。”
刘清宁想了想:“跟二舅家的事有关?”
吴楚楚沉默了片刻,“嗯”了一声。
两人同时沉默了下来,耳边只有呼呼的晨风卷进车里的声音。
亲戚们闻讯而来,已经把王永梅的病床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王向远根本挤不进去,耷拉着脑袋,蹲在病房外不说话。
这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老家村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男人,年逾六十,头发花白,脸上、粗粝的手上,都布满与其年龄并不相符的皱纹,整个等待的过程中,沉默木讷。
医生出来的时候,两个妹妹和弟弟都呼啦一声围了上去,七嘴八舌问东问西,他却始终站在外面,竖着耳朵凝神仔细听医生的话,双眼却是迷茫涣散的,显然,他并听不太懂医生在说什么。
弟弟王向高,年轻时候就携家带口去了深圳做生意,见过一些世面,只比王向远小三岁,却是截然不同的模样,虽也双鬓发白,但穿着西装裤,polo衫,蹬着一双皮鞋,头发、皮肤都散发着一种油润的光亮。
王美莲站在稍远的地方,在跟远在国外的大哥通电话。老大王向松在南美,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近亲都到了,只是徒劳地或站或坐,时不时地搭上一两句话。
此刻谁也不能做什么。
刘清宁一到,就被一堆亲戚塞到了病床前,王静的身边:“快看,宁宁来了。”
王静因为远道而来,又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国,得到了病床边最核心的位置。
床上虚弱的老人睁着混浊湿润的眼睛,茫然地朝着清甜看来,目光久久地定着,布满皱纹的脸上没什么神情,只有嘴角微微地颤动着。
刘清宁没想到一别十三年,再见外婆竟然是这样的场景。
记忆里的外婆,穿着蓝布衣衫,半花白的短发总是梳得很整齐,用两个黑色夹子别在耳后,精神矍铄,每天一大早去村口的老人活动中心搓麻将,非得搓到外公板着脸找来,才迈着小步子急急忙忙回家做饭。
而此时,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头发已经全白了,也稀疏了,此时因为一番折腾,已凌乱不堪。医院的病床不过一米宽,年迈的老人陷在发黄的被褥里却还空余,她瘦得仿佛只剩了一把骨头。
刘清宁的鼻子一下就酸了。
有人在背后推她:“叫外婆呀。”
可她张张嘴,曾经熟悉的两个字却卡在了喉咙里,嘴巴紧紧地闭住,仿佛涂了胶水一般。
好在并没有人坚持为难她,话题马上就转回到了王永梅身上。她在无人留意的情况下,退出了病床边的核心区。
一个和外婆年纪相若的老太太站在床对面,拍着外婆的肩膀,扯着嗓子中气十足:“儿女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面都没见着就走了?”
这一问把老人蓄在眼眶里的泪全拱了出来。
刘清宁真怕她手劲太大,一下子把外婆给拍散了。
病房里人多,刘清宁退到走廊里。她目光张望,瞧见吴楚楚正站在护士站前,跟护士说着什么。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男人,挺拔,清瘦。
“姐!”刘清宁走过去。
两人同时回过头来。
“见到外婆了?”吴楚楚问,将身边的咖啡递过来,“喝杯咖啡提提神,我朋友买的。”她指了指身边的男人。
对方朝她一笑,点头招呼,正要说话,手机响了,接着电话匆匆离开。
吴楚楚望着那背影,半开玩笑:“大领导,就是忙。”
四月的清晨,还有些冷。刘清宁坐在凳子上慢慢将一杯热咖啡喝完,精神才略略振作一些,医院里的脚步声也渐渐多起来。
一场令人期待的团聚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被提前了,但气氛并不愉快。
喧闹了一个上午,亲戚们来了一拨又一拨,流程大致相同,先看望了阎罗殿走一遭回来的老人,讲了一些大同小异劝慰的话,然后又拉住王静寒暄几句,轮到刘清宁的时候,一律都以“都长这么大了”开场,然后说一些她小时候的事,以“你还记得吗”结尾。
这些事,刘清宁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印象,但眼前的人,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但她也只能说:“哦,记得记得!”
也不管她是真记得还是假记得,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对面的人便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就此放过她。
末了,再约定王静什么时候上他们家里吃饭,回过去再劝慰老人几句,便正式结束了一次探视。
到了中午,两母女实在撑不住了,王美莲就让吴楚楚先送她们两个回酒店休息。
等她们走了,王美莲又安排王向远:“哥,等晚上楚楚下班,我让她去接阿静两女去我家,吃了晚饭,再让她送你回村里,妈这里晚上我看着就行。”
王向远“哎”了一声答应了。他平常就没什么主意,虽是哥哥,但对这个妹妹的话言听计从,在他的眼里,自己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人,一辈子在村子里,连市里都没去过几次,兄弟姐妹几个,都比他有出息,走得远见得多,他们懂的肯定比自己多。
探病的亲戚走了一波又一波,但似乎谁都没留意到王向远,虽然是他第一个发现老人家寻短见喝了药,是他把老人家送到了城里来。
怎么发现老人家服药,怎么敲开了驻村干部的门,怎么灌肥皂水催吐,把老人家一路送到医院......都以王美莲作为“发言人”,一一向亲戚们讲述交代。
没人注意到这个如木头一般坐在门口的“当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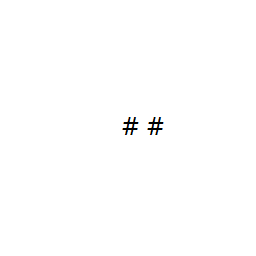
最新评论